| Blog信息 |
| |
blog名称:IDMer (数据挖掘者)
日志总数:175
评论数量:848
留言数量:119
访问次数:2497009
建立时间:2005年6月24日 |
| 我的相册 |
| |

|
| 联系方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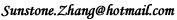 |
|

| |
| 公告 |
“数据挖掘者”博客已经搬家,欢迎光临新博客网址:http://idmer.blog.sohu.com
我的新浪微博:@张磊IDMer |
| 网络日志 |
|
互联网周刊:微软走过盖茨 |
|
|
|
|
|
数据挖掘者 发表于 2007/5/15 16:05:51 |
|
|
|
转自:《互联网周刊》
500)this.width=500'>
互联网周刊封面报道:走过盖茨
本刊记者赴西雅图微软总部,探寻“精神领袖”淡出之后微软的创新支点
盖茨之于微软越来越像是一个标签了,或者只是一个影子。他的渐渐隐退,也把微软一步步带入了“创始人缺失”的时期——尽管盖茨早在7年前就把CEO的位子让给了微软的第二号人物鲍尔默,但他作为“微软精神支柱”的实际影响力毕竟无可替代,再稳健和保守的交接方案,也很难削弱这种影响力。而且,如果鲍尔默也隐退了呢?
10个月前,雷·奥齐(Ray Ozzie)接替盖茨出任微软“首席软件架构师”,盖茨当时还宣布将会在2008年正式淡出日常管理工作,退居幕后,只留任董事长一职,更多的业余时间将致力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慈善工作。而盖茨 4月份隆重而匆忙的中国行,更像是一次超级巨星的走秀,他的淡然似乎给人一种“局外人”的错觉。
这仅仅是微软近几年来正在经历的、其公司历史上最为至关重要的两个转型中的一个。另一个转型来得更加迫切并毫无回旋余地——微软必须尽快从一家标杆式的软件公司过渡到一家售卖“软件+服务”的服务型软件公司,并且要有足够强的吸引力和执行力。
微软正在为目前所要经历的改变,全力打造更强有力的翅膀——革新在线服务业务的思维方式、完善研发体系、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高度关注中国市场。
微软在未来能否顺利渡过转型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大支点的稳固性。
微软之变
微软全球范围内的转型已经棋到中盘。比盖茨的淡出更加考验微软耐心的,是微软必须尽快从一家标杆式的软件公司过渡到一家售卖“软件+服务”的服务型软件公司。
3月中旬的西雅图,时不时就会被笼罩在一团细雨中。从太平洋东海岸源源不断涌来的大量湿润空气,给这里带来了充沛的雨水,天气也因此总是阴晴不定,甚至会在阳光普照的时候忽然飘起小雨。
一个难得出现的大晴天,让盖瑞·弗雷克(Gary Flake)的心情非常愉快。这位有着明星面孔的大男孩,早已习惯了加州的阳光和沙滩。两年前,他从生活了十多年的硅谷搬到了位于西雅图市郊的雷德蒙。虽然这座挨在西雅图东面的小城常年气候温润,但他刚来的时候,却觉得很不适应,也不喜欢。
生力军
促使弗雷克最终决定走出硅谷,搬离加州,并留在雷德蒙的,是来自微软总部的诱惑。
弗雷克在Overture(曾与Google齐名的著名搜索引擎公司,2003年被雅虎收购)工作了很久,后来还创建了雅虎实验室,当时,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微软开始认真的和他谈起了工作。“其实我那时和Google也有接触,包括和Google的两位创始人都深谈过。当时我面临三个选择:留在雅虎、去微软或者Google。”3月15日,在雷德蒙的微软总部,脸上撒满阳光的弗雷克,向《互联网周刊》记者回忆说。
弗雷克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互联网领域十几年的工作经历。弗雷克是马里兰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虽然年纪轻轻,但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自组织网络等研究领域大有名气,他几本有关网络搜索和数据挖掘的著作在过去的十年间流传极广,目前很多美国大学的计算机系都将其列为必读书目。Overture的成名,他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在进入雅虎后,又一手创建了位于硅谷的雅虎实验室(Yahoo!Research Labs),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互联网领域的“技术英雄”之一。
面对人生的选择,弗雷克陷入了思考。“如果我们看看这三家公司的步伐和行动方向的差异,你会发现Google和雅虎对于它们正在做什么、要做什么,方向非常明确和清晰。这也意味着,我想我很难有机会去改变什么。微软找我的时候说,公司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想要做出改变,并沿着新的方向前进。它们希望能找到像我这样的人,成为帮助它们进行‘导航’的人之一。”
这一点无疑对弗雷克有着最大的诱惑力,尽管他选择微软也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微软的名气和势力,以及“目前世界上最健全、最令人兴奋的面向基础研发的公司研究体系”。2005年,弗雷克加入微软,成为当时微软的“杰出工程师”(Distinguished Engineer)之一,主要负责微软研究院和MSN之间的技术产品集成,以及制订微软MSN门户、网络搜索、桌面搜索以及商业搜索的技术方向。一年后,他当上了微软的“技术院士”(Technical Fellow),这也是微软内部在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级别称谓,目前在全球只有18位。
弗雷克是微软近几年间大举招募的新鲜力量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和弗雷克的背景类似,在全美第四大搜索门户Ask.com担任CEO的史蒂夫·伯考维茨(Steve Berkowitz)在2006年4月跳槽到微软,出任高级副总裁。3个月之后,微软一个整合了Windows Live和MSN两个品牌的新部门——微软在线服务集团(OSG)正式成立,伯考维茨全面负责该集团的市场销售和商业拓展。“对于竞争对手,我们不仅仅是关注,而且还要找到击败它的方法。”在微软总部接受《互联网周刊》采访时,伯考维茨这样说。
最新的例子出现在今年1月。当时担任IBM软件集团首席架构师、并且也是IBM院士(IBM Fellow)的唐纳德·弗格森(Donald Ferguson)从IBM空降微软,成为微软目前的18位“技术院士”之一,主要关注信息技术在各种业务中的革命性作用,架构已有产品和新产品并引领方向。其实微软把弗格森从IBM挖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辅助10个月前正式出任微软“首席软件架构师”、在很大程度上接替了盖茨技术导师角色的雷·奥齐(Ray Ozzie)。有趣的是,弗格森和奥齐原来曾在IBM做过同事。
盖茨的接班人
奥齐的背景很有意思。他是盖茨的老朋友,两人在22年前就已经相识。当时,奥齐自己创建的Iris Associates公司刚满一岁,而且刚刚和当时著名的软件公司Lotus(莲花)签订了Lotus Notes的开发合同。奥齐之所以得以在当今的技术界声名显赫,并被盖茨所器重,主要就是因为这份合同。奥齐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为Lotus推出了第一个正式发行的Lotus Notes版本,这款最早问世的办公软件平台产品为Lotus和奥齐本人都带来了极高声望,奥齐由此也被誉为Lotus Notes之父。1994年,Iris Associates被Lotus收购;次年,Lotus又被IBM以35亿美元并购,Iris由此成为IBM软件集团Lotus品牌下的一个形式相对独立的部门,奥齐也随之成为IBM的雇员。直到1997年,奥齐离开IBM二次创业,创建了Groove网络公司,并一步步将其带入主流。
2005年3月,微软以1.2亿美元的现金收购了Groove网络公司,该公司的创始人奥齐随之进入微软。据说,由于奥齐与Lotus的渊源,IBM也曾经试图和微软竞购Groove,极力拉拢奥齐加盟,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微软。虽然具体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奥齐和盖茨的私交、以及盖茨对他的信任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去年盖茨宣布即将淡出微软日常管理的时候,除了奥齐被委以重任之外,时任微软CTO的克瑞格·蒙迪(Craig Mundie)也在名义上接过了盖茨的部分工作,出任微软首席研究与战略官,主要负责产品研发和制订技术策略。
与奥齐相比,克瑞格·蒙迪的经历要简单得多,而且外界对他也熟悉得多。盖茨去年在写给微软全体员工的信中这样评价他:“蒙迪和我已经一起工作了14年,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是一位技术预言家和策略上的领军人物。”这样的评价其实非常恰当。可以说,正是由于蒙迪在几年前发起和促成了微软的“可信赖计算”计划,才使得微软日后在处理垄断、开源、知识产权、安全等等棘手问题时,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和方向。同时,他还领导了微软推行的“政府安全计划”(GSP),并大力主导了对Linux社区和Sun采取“怀柔”政策,促成了微软近年来与欧盟、苹果、Sun、IBM的一系列诉讼和解案,为微软营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的外部环境。蒙迪的种种判断深刻的影响了微软近年来的发展战略,甚至部分改变了微软的价值观。
“我们很稳定的中心是没有变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很明确,CEO就是鲍尔默,我们不是在一种飘摇的状态里大家竞争,而是很有序的培养一批人出来。”4月13日,在接受《互联网周刊》独家专访时,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兼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陈永正这样说,“而且,盖茨自己是准备从一个全职的状态,变成兼职的董事长。在这样的转变里面,他还是会抓大的方向,在商业方面会慢慢淡出来,但是在研发和产品开发的大方向他还是会去抓,并没有放掉。他希望能集中在这两年内,把一些重要的软件和未来的技术架构定下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智慧。”
你还可以发现盖茨的另一点智慧所在:他选择交权的两次时机,一是7年前把CEO的位子交给鲍尔默,当时正值Windows 2000发布前夕;而宣布卸任“首席软件架构师”和淡出计划的时候,Windows Vista又即将登场。照例,这样的时期往往是华尔街对微软信心爆棚的阶段,可以大大稀释投资者对微软高层变动的注意力。华尔街对微软人事变动的态度证实了盖茨的智慧。这10个月以来,微软的股价上涨了近30%。
今后数年内,一个由奥齐、蒙迪和鲍尔默所组成的“铁三角”将会逐渐取代盖茨而成为决定微软前进方向的直接推动力。这一步看似简单,实则暗藏变数。
“从公司政治的角度来看,在微软内部,奥齐的份量肯定不如盖茨,鲍尔默则并未被视作技术灵魂。”在沃顿商学院去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该学院信息技术组的高级主任肯德尔·怀特豪斯(Kendall Whitehouse)说,“鲍尔默和奥齐将如何在短期战术和长期战略之间进行折衷呢?在决策方面的权力如何划分界限呢?这些都将是很有意思的事。”而对于盖茨,沃顿商学院领导力项目组的主任伊文·维滕伯格(Evan Wittenberg)则认为,他的挑战将是“如何既能在他毕生奋斗的公司中保持影响力,又不会介入过深”。
转型之困
其实,对于任何一家带有强烈创始人风格的商业公司而言,这一“创始人缺失”时期都是其必然要面对和渡过的敏感期。无论是早年间的IBM、惠普、迪士尼、英特尔,还是现在的Sun、苹果、Oracle,其创始人在位与不在,对公司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盖茨当然很明白这一点,他在7年前就开始的让权、并尽可能简化公司内部政治局面的决定已经说明,盖茨希望自己之于微软的意义能够渐渐的像是一个标签,或者只是一个影子。
留给盖茨过渡时间还有很多,到今年10月他不过才52岁。这仅仅是微软近几年来正在经历的至关重要的两个转型中的一个,也是不能急于求成的一个。另一个转型则要迫切得多,而且更加凶险并毫无回旋余地——微软必须尽快从一家标杆式的软件公司过渡到一家售卖“软件+服务”的服务型软件公司,并且要给出足够强的说服力和执行力。
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回顾过去的十年,你会发现,微软是一家标杆型的产品型软件公司,Windows和Office一直都是其最主要的利润支柱。但在最近几年,以Google、Salesforce等新星公司为代表的软件服务化势力,用一种崭新的角度,迅速瓦解着传统商业软件的销售模式。IBM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有所觉察,并开始朝着这一方向转型,但它的领域并不包含应用软件,也不与最普通的消费者接触,并把重心定位于为这类转型的公司提供全套改造方案。而Google们却完全不是这样,它们迅速吸引了数量惊人的用户群,而且是具有很高粘性和忠诚度的用户群,靠“长尾效应”赚钱。
根据今年1月微软发布的200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由于受Vista和2007 Office推迟发布的影响,在截至2006年12月31日的这个季度内,微软只取得了26.3亿美元的净利润,同比下滑28%。在目前微软独立计算财务的五大业务部门中,2006年7月刚刚重组而成的微软在线服务业务部门的营收为6.24亿美元,不仅大大低于客户端、服务器和工具、商务、娱乐和设备等其他四大业务部门,而且运营利润亏损1.55亿美元,降幅最高。
虽然微软的生命线在短期内并不会倚重于此,但包括盖茨在内的微软众高层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在线服务业务将是微软未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支点。鲍尔默经常喜欢在内部员工大会上“咆哮”着对一个词汇连续重复三遍,最近几年,他“咆哮”最多的词已经变成了“广告!广告!广告!”
微软会变成一家互联网公司吗?资本市场一直在期待微软的新答卷。2006年4月底,微软宣布将大幅增加对于互联网和软件服务等领域的长期投资。华尔街上空开始飘荡起“微软即将收购雅虎”的流言。一时间,资本市场反应强烈,微软的股价在短短的3天内暴跌近15%,并很快在6月初跌破22美元,创出自2002年8月以来的新低。众多分析师口径一致的认为,虽然微软的盈利能力勿庸置疑,但这笔开支究竟将如何支配非常耐人寻味。收购雅虎?那简直不可想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尔街当时的不安正体现出,外界对微软在互联网和软件服务等领域内的表现早已期待多时,甚至已经快失去耐心了。微软在2005年抛出“Live战略”,就像其在2000年抛出“.NET战略”时的情景一样,所有人只是朦朦胧胧知道微软想做什么,但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微软会怎么做。
下一站:Live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将近一年,就在微软的股价跌破22美元之后,微软终于开始了正式行动。
2006年6月19日,微软在全球超过60个市场发布了首款Windows Live品牌下的网络服务产品Windows Live Messenger,宣告Windows Live的具象化行动正式开启。7月,微软又宣布微软在线服务集团成立,并把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并列为全球四大重要市场。此后,从品牌的角度说,MSN将特指内容平台,也就是MSN门户网站;而Windows Live则指服务平台,其中还包括了微软专门为此搭建的Live.com。一个“软件+服务”的雏形由此诞生。
“‘Live战略’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Live平台,个性化的Live服务,以及基于互联网的Live体验。”在接受《互联网周刊》采访时,伯考维茨这样解释“Live战略”的内涵。弗雷克的答案是:“Windows Live是一种软件和服务的组合,可以帮助微软建立一座连接用户价值、终端设备和在线服务的桥梁。”
直白的说,在“Live战略”的框架下,微软将为普通用户提供一种多重的整合性体验。横向上看,Live平台不仅包括Windows、Office、Xbox,将来还会有CRM Live甚至是ERP Live出现;纵向上看,每一种Live平台之上,又会集成多样化的互联网服务,比如Windows Live品牌下,微软目前已经推出了即时通讯、博客、搜索、分类广告、安全等在线服务。按照伯考维茨给出的路线图,排在微软日程表上的Windows Live服务产品还有二十多种,都将在今明两年内陆续发布。其中有些是对老产品进行了新包装,有些则完全是全新的。
微软的核心层也开始渐渐把“Live战略”置于更高的重要等级。“Live平台是微软未来最重要的项目。”鲍尔默说,“而在下一个层面,互联网服务和在线体验将会随之提供给消费者。我们正在进行这样的迁移。”“Windows Live对我们而言是个新鲜事物,现在由奥齐直接负责。”今年年初,盖茨在接受CNET采访时承认,“Live战略”对微软确实是个挑战,“现在Vista已经上市了,我们下一步将有更大比例的研发费用投入到Live应用上,明年用户就将看到一些新的服务产品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突破。”
陈永正告诉本刊记者:“我相信再过几年,延续这样的思路做下去,如果平台搭好的话,那在我们提供的这些Live服务方面,微软都会具备竞争力。”今年3月14日,微软和联想集团共同宣布了一项全球性协议,将在今后销售的联想电脑中预装Windows Live服务,包括Live.com门户网站和Windows Live Toolbar工具栏。这也意味着,微软的下一站将会全力投入Live战略的落实。
实际上,微软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为此做起了实质性的准备工作。当时的Google虽然还没开始演绎其“暴富神话”,但来自于方方面面的迹象已经让微软非常警觉。当年,微软陆续终止了与雅虎和Inktomi在搜索方面的业务合作,决定正式进军搜索领域,并在其研究院体系中逐渐调整了研发的重点,适当对与搜索和互联网应用相关的技术研发做出了倾斜。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在2005年10月成立的互联网搜索技术中心,其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优化微软在互联网领域内的创新,并加快技术产品化的速度。
像弗雷克和伯考维茨这样的业界精英,都先后成为微软在加强在线服务实力方面的重要棋子。弗雷克很快就联合了MSN和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资源,于2006年1月在微软内部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实验室——“Live Lab”,直接定位于新技术的产品化,弗雷克告诉记者,这座实验室的目标是“要在技术和工程间发现有价值的结合点”。几乎同一时间,微软直指在线广告市场的实验室“adCenter Lab”也在微软总部宣告诞生。4个月之后,微软推出“adCenter”服务,正式开始和Google的“adWords”和“adSense”抢起了在线广告的生意。
虽然微软到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掌握主动,并且也没在搜索的市场份额上削弱Google的实力,但你不难体会到微软的野心。“微软专注于互联网技术这一事实显示,它不希望在下一轮技术进步中再次丧失良机。”多年来以研究微软发展而著称的独立研究机构“Directions on Microsoft”的首席分析师马特·罗索夫(Matt Rosoff)说,“此举非同寻常,微软已经在密切地加强其研究人员与其产品集团之间的关系,希望其研究成果能迅速转换为产品进而再变成现金。”
其实在微软研究院内部,自2001年至今,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名为“微软技术节”(TechFest)的内部技术交流会,由其各个研究院选送研究成果,汇集到总部进行现场展示,只要是微软员工,提交申请就可随意参观。而在3月初刚刚结束的TechFest 2007上,微软破天荒的将其部分新成果对外界开放。在现场你能看到五花八门的演示,覆盖面极广,或高深或生活化,或结构复杂或构思巧妙。每年的技术节,微软的高层都会自发性的到场参观。负责微软研究院的资深副总裁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这样告诉记者:“技术节能够让人们了解和体验到我们所追求的软件创新的边界。”而更实际的意义是,微软也希望能借TechFest对外界开放的机会,吸引潜在技术合作伙伴的注意。
微软式创新哲学
对于微软的下一场战役,似乎并没有太多人会真正去关心它最终会不会成功。因为在微软走过的近32年中所发生的无数实例证明,微软最不缺的就是耐心。无论是Windows、Office、IE、MSN、Xbox,还是互联网搜索、Zune,微软的每一步都不是以开拓者的姿态走出的。甚至,恰恰是由于环境发生了改变,前人已经做了尝试并且有了收获,微软才得以采用自己擅长的创新方式去捕获成功。陈永正认为,这其实也正体现了微软的创新哲学。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技术创新,如果技术不创新,你不可能赢。”陈永正说,他对微软在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转型,始终都很有信心,“微软可能不会有像苹果的iPod那么强的某种产品,但是我们在面上铺得更广,平台是我们的核心。这是微软不同于其他公司的哲学。”
遵循这样的哲学,微软目前正在做的主要努力,一方面是构建和完善适应新局面的应用和服务平台,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多的争取消费者,并留住他们。这也是微软之所以在近几年间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即BRIC,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快速发展的市场)投以高度关注的根本原因。
微软自己从来不否认其在搜索领域的迟到,在对于搜索背后所蕴藏的高达千亿美元级别的在线广告市场,微软一直坚称自己的切入时机并不晚,包括盖茨在内的高层们多次强调:“整个在线广告市场目前还仅仅处于萌芽期。”既便是搜索,微软同样希望自己能后来者居上。而且微软在研发投入上从来都出手豪绰,比如其在2007财年的研发投入就高达70亿美元。
“只有微软有机会完全改变目前的搜索技术现状。”弗雷克对《互联网周刊》说,“我在搜索领域内已经工作了多年,在这段时期内,我个人是觉得失望的——我们仍然在用文本框,我们对于用户想要得到的高质量、精准的搜索结果,仍然有较低的满意率。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雅虎还是Google,它们要想对搜索体验做出本质性的改变,都不可避免的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它们最核心的业务都要基于用户体验和用户粘性之上,它们很难会主动的做改变。”
弗雷克还提到了微软的另一个优势:“微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健全、最令人兴奋的面向基础研发的公司研究体系。”
身为这个庞大体系中的一份子,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以让人对微软的创新哲学有更加形象的理解:“创新就是把你推到悬崖边上,问你还敢不敢再往前跨一步。创新注定是十分艰难的工作,需要一种文化和环境以及人的冒险精神。”现在,Google们已经把微软逐渐推到了悬崖边上,这一次,微软又将如何演绎它的创新哲学?
微软的创新支点
从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最近几年的变化上,你不难体会到微软研究院之于微软的意义所在。
陈正非常健谈,而且语速极快,逻辑流畅,几乎出口成章。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背景,你很难想象,面前这位一点也不“讷于言”、并且略显瘦弱的年轻人,会是个非常标准的“搞技术的人”。陈正1999年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毕业,主要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当年,他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 Asia)的前身。由此成为微软在中国最早招募的一批研究员之一。
至今,陈正已经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度过了8年时光,也逐渐从当年还稍显稚嫩的副研究员,一路晋升为主任研究员。本刊记者在今年的微软技术节(TechFest)上碰到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和首席科学家沈向洋时,他说:“你有空和陈正聊聊吧,他在研究院的这8年,不仅见证了我们团队的成长,而且他个人的进步也很快。”
坐在陈正那间有些凌乱的办公室里,听他像讲故事似的回忆过去,如果不打断他,你几乎就插不上嘴。
一个样本和一座研究院
像所有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一样,陈正初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方向。当时,研究院有几个研究小组:语音、多媒体、视觉计算、自然语言、以及用户界面。陈正选择了做语音识别,更多侧重于统计语言模型。“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语音输入法,另外还有一个可以根据上下文自动识别的文本输入法。”他说。
很快,陈正和他的同事们在语音模型的研究到了一定阶段,决定把研究方向转到搜索,当时是2001年。后来在马维英博士的带领下,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网络搜索正是他们探索的领域之一。
2003年,无论对陈正,还是对亚洲研究院或是整个微软研究院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就在当年,微软决定正式进军搜索领域,并陆续终止了与雅虎和Inktomi在搜索方面的业务合作。当时恰逢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五周年。
那年夏天,陈正和他的两位同事到微软总部去参加了一个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与雷德蒙研究院共同组织的搜索夏令营。“我们认识了公司很多产品组的人。由于当时公司刚刚进入到在线广告领域,我们很兴奋的发现,其实产品组遇到的很多问题,和我之前在做对用户进行个性化刻画研究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很像。包括如何刻画用户、如何描述、如何针对用户提交和推送相匹配的信息。”
于是双方相见恨晚,一拍即合,正式为此设立了一个研究课题。与此同时,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式将网络搜索与数据挖掘列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这也就意味着,此项研究不可能一个人去实现,因为其中不再仅仅涉及技术,还需要有产品方面的支持。从那时起,陈正自己开始了独立做研究的阶段,被提升为项目负责人及主任研究员。
因为有前两年的研究做基础,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陈正和同事们就研究出了很多算法,并被当时MSN部门的相关产品组拿去转化成了产品, 对新成立的“adCenter”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adCenter”产品组又和微软亚洲研究院联手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新的产品孵化中心“adCenter Labs Beijing”,这也是微软总部以外设立的第一家针对在线广告研发的实验室。
从陈正的经历中,你不难发现微软亚洲研究院在最近几年间的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在2005年10月正式成立了互联网搜索技术中心,其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优化微软在互联网领域内的创新,并加快技术产品化的速度。而这些变化也恰恰折射出微软研究院之于微软的意义所在。此外,亚洲研究院是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设立的第二家基础研究机构,并且目前也是除雷德蒙研究院之外,微软研究体系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从很低调到露锋芒
微软最早的一家研究院是1991年在其公司总部成立的雷德蒙研究院,这里至今仍然是微软的研究重镇。据说当时的提议是由时任微软CTO的奈森·迈尔弗德(Nathan Myrvold)直接向盖茨提出的。那个时代的微软,远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产品线,同样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强敌。
经过16年的发展,微软已经先后在全球建立了5家规模各异的研究院,研究领域各有侧重,比如剑桥研究院就致力于“将学术推向极致”,而雷德蒙研究院和亚洲研究院则会更多的侧重技术与产品紧密结合。每家研究院的院长直接向负责微软研究院的资深副总裁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汇报,而雷斯特再直接向盖茨汇报。盖茨宣布退休计划后,微软研究院现在主要是向微软首席研究与战略官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汇报。
3月初,微软在位于雷德蒙的公司总部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技术节。在两天的时间里,共展示了来自微软全球5大研究院的120多项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亚洲研究院带来的40余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新成果中约有1/3对外界开放,这在微软历史上尚属首次。已经举办过的6次技术节,观众都仅限于微软内部员工,主要目的是让微软产品部门的人可以零距离的接触到微软研究院的各种研究成果,从而为技术产品化提供便利。
“技术节能够让人们了解和体验到我们所追求的软件创新的边界。”雷斯特在开幕式上说。除了官方说法之外,微软的行动还有更深层的意味。首先是对竞争对手施加压力,产生威慑作用。“就在微软为了击败Google而努力研发新搜索技术的时候,它选择打开公司大门,让外人能够直观感受其公司文化,这种形式本身就已经超越了Google。微软对TechFest的开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来自旧金山湾区的独立观察家Brad Neuberg评价说,“在旧金山的湾区流传着这样一个玩笑。如果你在某次聚会上遇到一位Google的员工,你问他在哪儿工作,他多半会回答说‘我不告诉你’。而对于微软和雅虎的员工,你就很少会碰到类似的情况。”
另外,此举还有很现实的意义。微软研究院每年都会新增数百项的研发成果,这些不可能全被微软产品化,对于大量闲置的技术成果,微软想出了一个技术转让的双赢方案——IP Ventures(专利技术合作项目),把技术拿出来面向全球转让。该项目于2005年5月启动,国内的两家公司科通与拓维在去年成为了该项目在中国的首批合作方。
去年9月,微软为其研究院成立15周年举行了庆典仪式,并给出了这样一句口号:“15年来,我们一直在把想法变为现实。”而现在,从想法向现实的转变又多出了一道途径。
微软基因被中国改变
对于中国这块非常特殊的市场,微软曾经爱恨交加,但现在却愈发显得轻车熟路。不是微软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改变了微软。
河南省漯河市的街道上,前几天出现了两辆很奇怪的大轿车。从外面隔窗看过去,车厢里不像普通的客车那样有一排排座位,而居然摆着一排排电脑桌,而且桌上还放着电脑!
这并不是电影道具,而是微软在4月23日捐给河南省政府的两辆“信息大篷车”。每辆车上配备有16台电脑,并有专职IT指导教师,微软将其称为“流动的信息技术培训教室”及“流动的信息服务站”。同一天,微软捐赠的“河南省漯河市信息化培训基地”也正式揭幕,其中容纳了50台配有网络连接的电脑。而在此之前的4月19日,类似的场景也在四川成都上演过一次。
不出人意料的是,微软公司资深副总裁兼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陈永正出现在揭幕仪式现场,在他旁边还站着微软首席研究与战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 Mundie)—微软核心管理层中来过中国次数最多的人之一。最近3年多来,像这样带有某种特别意味的仪式,总是面带灿烂笑容的陈永正几乎每次必到,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他究竟参加过多少次诸如此类的活动。
“这是我加入微软三年多来最忙的两个月。”4月13日,一脸笑意的陈永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感慨,眼神中有些淡淡的疲惫。
看看陈永正在4月的行程表,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疲惫”。在去漯河的前一天,他刚刚在海南博鳌把结束第10次访华的盖茨送走;前四天,他和盖茨一起出现在北京举行的微软亚洲领导人论坛现场。而4月初,他在上海和宝信软件总经理陈在根签下了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谅解备忘录。类似的情景3月初也在杭州上演过一次,当时和陈永正握手的是浙大网新总裁史烈。
再加上微软的财年开始于每年的7月,所以这两个月原本就是刚刚完成中期工作汇报,并准备做下一财年计划的例行繁忙期,公司内部的大会小会不断,还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准备盖茨访华的相关事宜。以前业内曾戏称微软中国领导人的位子“是块烫手的山芋”,仅仅只是从上面提到的这个侧面,你就已经能感受到其中的滋味。
良性循环的起点
其实,陈永正3年来一直都在愉快地忙碌着。自从他2003年9月空降微软出任微软大中华区CEO一职之后,在陈永正面前,原本桎梏微软中国的一系列屏障一一土崩瓦解。无论是政府关系、正版化、合作伙伴、OEM厂商,还是业务增长、研发、大学合作和公司形象,微软目前在中国的状态都空前和谐。
“微软对中国的策略,与对中国过去这些年的耕耘和投入,现在开始产生了成效。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果要为这个循环找个起点,陈永正觉得那应该是微软在2002年,由时任微软CTO的蒙迪委托麦肯锡公司所做出的一份关于中国软件产业的调查报告。当时的这份白皮书,给微软和中国软件业都带来了思考问题的崭新视角。“等于是开了一条路,确立好方向,我们再来谈具体的。”陈永正回忆说。
很快,鲍尔默在当年6月访华,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即发改委)签署了关于软件产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承诺“与中央和各地政府以及产业界广泛合作,帮助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在战略合作、技术合作、人才培训、软件外包等领域投资62亿元人民币。一份白皮书和一份备忘录,成为微软中国走入快车道的起跑线。
也正是从那时起,微软看待中国市场的态度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尽管微软在多年前就将微软中国视为除美国总部之外,微软在全球功能最完善的一家子公司。中国市场如此特殊,又如此复杂,这里的问题远非换几任中国区负责人就能轻松应对的。
2002年年底,微软总部专为中国市场成立了微软中国顾问委员会(China Advisory Board),其成员为当时所有的微软资深副总裁。顾问委员会成立伊始,便决定将在微软大中华区设置CEO一职,统管微软在中国的一切事宜,并准备把微软大中华区从亚太区独立出来,设立一个单独的大区。而且由于微软公司本身的特性,需要一位既熟悉中国市场,又擅处理关系,并且还要有跨国公司背景的职业经理人,当时的摩托罗拉(中国)董事长兼总裁陈永正由此进入了微软的视线。
陈永正当年在接受这个领导小组面试的时候,问他们怎么看待中国市场,结果那些资深副总裁们非常清楚的回答:这是除了美国以外微软最重要的市场。他“当时觉得很振奋。”2003年9月,陈永正上任。10月,微软大中华区正式从亚太区独立,直接向总部汇报。
实干主义
“三年来,(微软中国)大的布局和策略已经比较清晰。我来以后,只是在执行层面将策略更具体地布局和落实,点、线、面都要连到一起—我们跟中央的部委的合作,然后是与合作伙伴的合作,然后再到地方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技术中心。”陈永正如此描述微软中国在近几年来所实现的良性循环,他并不觉得个人在其中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如果说跟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不但要执行总部最早制订的思路,同时还会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把它更具体化。关键就是和总部的密切沟通,这样才能把这几个战略连续执行和贯彻下来。”可以看出,在“陈永正时代”的微软中国,“执行”是首当其冲的关键词,而陈永正无疑是“执行”高手,他在不同场合使用频率最高的句式—“扎根中国,与……共同成长是微软的长期承诺和核心战略”,其中“……”总会很合时宜的换成“中国”、“中国软件业”、“合作伙伴”等等—也绝非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自2005年开始,微软在一年内先后对浪潮软件、中软国际以及大连华信等多家国内软件公司投下重金,总额接近1亿美元;而自陈永正上任以来至今,微软已在中国陆续签下了6家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并且还在前不久推出了直接针对企业合作伙伴制定的“深耕计划”。
很直观的例子就发生在一年前。2006年4月,在两周的时间内,国内四大PC厂商联想、方正、同方和TCL,先后与微软签订了巨额采购协议,总计高达16.3亿美元。随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的第一站就选在了位于雷德蒙的微软总部。而克瑞格·蒙迪和鲍尔默在2006年4、5月间先后访华,都带来了极有份量的“礼物”。
蒙迪拿来了“未来5年累计1亿美元的软件技术支持、软件开发和软件测试服务订单以及每年超过7亿美元的硬件产品出口订单”,另外微软公司还将投入1亿美元,与中国境内的软件企业及其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合资公司等进行合资、合作,利用微软公司的资源优势和经验支持中国软件企业发展。
鲍尔默则承诺,在未来5年内,微软与中国信产部的合作总投入价值将不少于2.5亿元,同时,微软还将为与信产部协商确定的3家中国软件企业提供对口咨询服务和定制化培训,并为其争取价值2.5亿元人民币的外包订单。前面提到的“信息大篷车”,就正是去年5月微软与信产部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中的一部分。选择在盖茨访华带起的热潮期将其带到台前,足见微软的良苦用心。
与微软中国在最近几年间的活跃遥相呼应的是,微软在全球范围内也在不断做出重大转变,无论是对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诉讼、与竞争对手的关系,还是对Linux、在线业务,微软都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去面对并尽一切可能的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市场又给了微软惊喜。
“我们在推行正版化和OEM预装正版软件的时候,告诉用户正版软件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分析,并进行了正版软件的宣传,告诉大家它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升级比较好。现在中国这里的做法已经被微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金砖四国’都在做。”陈永正笑了笑说,“有些国家很羡慕我们,说中国政府居然还会出台一项针对正版软件的政策。在这方面,中国市场也算是给全世界带来了一个正面的促进。” |
|
|
|
阅读全文(5205) | 回复(1) | 编辑 | 精华 |
|
|
|
|
|
|
|
回复:互联网周刊:微软走过盖茨 |
|
|
|
|
|
徐涵(Han Xu)发表评论于2007/5/15 18:34:36 |
|
|
|
Gates创造了微软帝国,微软为人类贡献了Office这一伟大的软件。但是现在,微软根其他上市公司没有什么分别,同样是为股东争取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创造更多伟大的软件。 |
|
|
|
个人主页 | 引用回复 | 主人回复 | 返回 | 编辑 | 删除 |
|
|
|
|
|
| » 1 »
| |